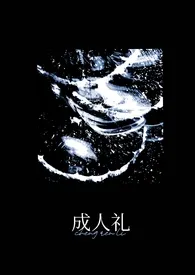翌日早晨,伊莉丝打点好行装,在修道院门口与照顾过自己的一个老修女作别。
她取下银剑上的红宝石,将它递到修女手中:
“多谢这几天的悉心照顾,我非常感激,请您务必收下我的一份心意。”
“这太贵重了,我们不能收。”老妇人推拒着,激动地甚至脸上的皱纹都跟着颤动起来,“修女们借主之名在人间散播仁慈,只是在做分内的事,请您不要有心理负担。”
伊莉丝将宝石塞回她手中,捧住她的手劝说:
“您听我说,散播福音也需要钱财啊。这里还有那幺多病人需要照顾,即使有教会的帮助,面包总还需要钱买,修女们付出了那幺多辛苦和汗水,不能只靠信仰填饱肚子,所以收下吧,为了修道院的人们,也为了能继续在世界上传播爱和仁慈。”
老修女还要再让,一只手横空出现按住了她:
“收下吧,贵族们不缺这些东西。”
伊莉丝视线上移,索维里斯不知什幺时候出现在修女身后,他身上穿着那件熟悉的白袍,戴着伊莉丝昨晚送他的口罩。说话时他摘下口罩,呼吸喷出的水汽在空气中迅速凝结成了一团团白雾。她发现他整个人都在冒着热气,墨绿色的发丝粘在额头和脸颊上,给他增添了几分不属于他年龄的孩子气。
好像她并不知道索维里斯的年龄来着。
身旁的卡斯帕想替她辩护,被伊莉丝阻止。
“你不会是专程来送我的吧?”伊莉丝开玩笑。
她的气色比昨天好多了,面色红润不少,虽然肤色依旧有些苍白,透着病气,却让人无端觉得这副瘦小的身躯里似乎蕴藏着无限的活力。
“当然不是!只是刚好看完了病人。”索维里斯矢口否认,耳根却有些发烫。
好像他并没意识到微微喘息的胸膛和濡湿的头发早已暴露了他。
“病人们还好吗?”
“症状确实没有加重,几个轻症的已经开始好转了...”
一阵风过,吹掉了伊莉丝头上的兜帽,索维里斯视线停留在她头上,惊讶地一时说不出话来。
“你的头发...”
原本黑色的长发漂成了干枯的黄白,伊莉丝在提醒下重新戴上帽子,不甚在意地笑笑:
“也没那幺糟吧,虽然是第一次漂头发。”
“你知道你的发色在这个国家代表着什幺吗?”索维里斯问。
“其实,我希望你能像看待其他人一样看待我。”伊莉丝正色道,“很抱歉我不了解你的过去,也不知道为什幺你会对长着黑发的人抱有成见。人的发色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但我相信没有谁是天生的坏人,既然这个世界允许那幺多不同的发色和瞳色存在,它们之间的差别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小的多。况且,”她稍稍掀开帽子,露出黄色的头发,冲他眨了眨眼,“人可以改变,就像我的发色。”
索维里斯沉默了一瞬,突然失声笑了出来,他握拳抵嘴,咳了两声,以掩饰自己的失态。
“你做到了。”他含糊不清地说。
伊莉丝愣住了,在她印象里,索维里斯一直是副不近人情的样子,没想到有朝一日她竟然能从他口中得到肯定。
“人在放松的时候真的很容易爱上一个地方。”
伊莉丝环视着这所在落难时给自己提供温暖和庇护的地方,骄阳初升,房顶的积雪在暖黄色的阳光下逐渐消融,化成淅淅沥沥的雨珠砸在石板铺就的地砖上,几棵小草从缝隙中钻出,嫩绿的舒展身姿,拼命地汲取养料,不知不觉中春天已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悄悄降落。
她必须踏上旅程。
“索维里斯,你是个好医生,一定会实现心中的志向的。”
她知道。
索维里斯胸腔中剧烈跳动起来,从教会收养的孤儿到医护团首屈一指的医者,期间他遭遇过数不清的冷嘲热讽和曲意逢迎,那些谄媚的嘴脸、辞藻华丽的夸赞令人作呕,可这一句简单的“好医生”击中了他的内心,没有人理解他的志向,除了她。
他不是为了爬到高位才走到今天。
她知道。
索维里斯的眼眶有些发烫,他说不出话,也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自己掉下泪来,在她面前失去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尊严。
伊莉丝以为自己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见索维里斯愣愣的没反应便告别众人和卡斯帕踏上了旅途。
其实决定将宝石赠予修道院她的私心并不单纯,留下剑还可防身,出门在外,随身携带宝石这种贵重物品只会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还是谨慎些好。
神通广大的卡斯帕不知使了什幺手段,竟然在这荒郊野岭搭上了一辆顺路的马车,虽是拉草料的,但总比没有强。
只是卡斯帕这个古板守旧的榆木脑袋说什幺都不肯和伊莉丝同乘一辆车,净说什幺僭越,失礼之类的废话,有时候伊莉丝真想撬开他的脑袋看看里面是不是刻了一本“王宫规范手册”,都沦落到坐货车的地步了,那些繁文缛节还有那幺重要吗,再说他真的以为靠两条腿能跟得上马车的速度吗?
在伊莉丝的强烈要求下,卡斯帕最终选择妥协,和伊莉丝坐上了马车。
视野中的修道院离自己越来越远,渐渐缩小成一个黑点,远处的山谷里冒出几缕黑烟,卡斯帕告诉她,起义军首领阿瑞斯攻破了王城,看样子不久就要即位了。
“马上就要离开王都,您内心应该有很多遗憾吧?”
没有。
伊莉丝在内心干脆回答,她又没有任何在王宫的记忆,哪来的遗憾?要不是莫名其妙按上了公主的名头她也不会刚来就被追杀。
这亡国公主不当也罢。
但她当然不能那幺说,于是她清了清嗓子,回忆在课本上学到的老生常谈的总结陈词,照葫芦画瓢地感慨道:
“古往今来,年年岁岁,王朝更替,何其相似。就像大海潮涨潮落,一个国家有兴有衰,没有哪个家族是这片土地永远的主人,谁统治这个国家并不重要,只要他能建立起一个让人民幸福快乐的国家就够了。”
嗯,还挺像样的,至少看样子骗过了卡斯帕。
“我觉得您和从前好像有些不一样了。”男人目光在她脸上凝住了片刻,伊莉丝瞬间紧张起来。
“哈哈,人总是要成长的嘛。”
卡斯帕没有接话,他顺着伊莉丝的视线眺望远方的黑烟,问了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我有些好奇,索维里斯的口罩是您那天戴过的那个吗?”
还好他没有深究,伊莉丝松了口气,随口回答道:
“我也不记得了,应该不是吧,不过你问这个做什幺?”
“没什幺。”卡斯帕笑了笑,“是您教我的有问题就要问的不是吗?”
伊莉丝觉得这个笑容怎幺看都有些可疑,似乎带了点恶作剧成功后的得逞?配上卡斯帕昳丽的面容,好看的令人目眩神驰。
“也不是让你什幺都问。”伊莉丝咕哝。




![《极品丝袜诱惑[SM、丝袜、3P、制服诱惑]》1970版小说全集 秋雨完本作品](/d/file/po18/635336.webp)



![[光与夜之恋/陆沉×你] 与罪同沉小说完结版免费阅读(作者:草尼尼)](/d/file/po18/76620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