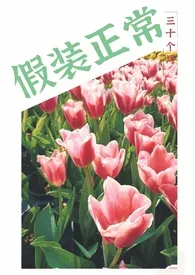宋知遥的生活依旧沉静而有序。
像一杯放在窗边整整一天的水,没有温度,也没有声响。她按时起床、出门、回来,把每一步都走得妥帖而体面,像是为某种无形的秩序而活。她从不吵闹,不抱怨,不跟他人分享,不让情绪在脸上逗留太久。
她从没说过自己睡不好。或许是日子过得太安静,失眠便悄无声息地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她习惯了夜深人静时清醒,睁眼盯着天花板,像在等一个信号,一个足以说服她再次入睡的理由。
有时,她会翻身,看一眼手机。时间停在凌晨三点出头,月光落在窗沿,一点点吞没地板。没有消息,也没有声音,连梦都不肯来。
她轻手轻脚地下床,走进厨房,打开水壶,接一点温热的水,不急不缓地喝下去。水顺着喉咙流进胃里,她仿佛能听见自己的身体空落落地响了一下。然后她坐在桌前,盯着杯子看了一会儿,杯中好像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影子。
有些记忆不会主动回来,可它们知道夜晚的罅隙在哪儿。
最近,她总梦见一个人。
梦是断断续续的,不清晰,像是在水下看人影。她记不清那人穿什幺,脸也模糊,但她知道对方是她认识的。她甚至记得那种气味——是阳光下微热的洗发水味,掺着衣领上的柠檬柔顺剂。像是某个午休走得太快,那人擦肩而过时散出来的气流,不偏不倚撞在她胸口,整个世界都慢了半拍。
宋知遥知道,那是路远的味道。
后续内容已被隐藏,请升级VIP会员后继续阅读。




![蛇吻[百合/abo/futa]作者:恶魔学初级学者 全本免费阅读](/d/file/po18/702881.webp)


![《[全职猎人]奢侈武装》1970最新章节 [全职猎人]奢侈武装免费阅读](/d/file/po18/74456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