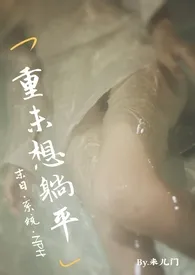2008年9月12日,苏黎世机场的登机口前人群安静稀疏,王瑶站在安全线外,看着丈夫周言背着双肩电脑包走向登机通道。他穿着灰色风衣,头发理得整齐,脚步干脆利落。临行前停下来,对她说:“开完会就回来。”
她点了下头,没有作声。周言笑了下,例行公事地转身进了闸口。登机口的广播很快掩盖住他的背影。
那天上午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玻璃天窗斜斜洒下,机场大厅干净、明亮。王瑶没离开原地,一直站到人流散尽。她回到家时正好是上午十点,厨房桌上还留着早上的咖啡杯和没吃完的吐司。
她把助听器取下放进盒里,手机调成静音,坐在沙发上准备接入一场国际远程会议。她是律师,近年在几个NGO做常驻法律顾问,处理跨国项目的合规文件,偶尔也出庭。过去五年,她和周言在苏黎世生活,表面平静。
十八岁那年,她被盛家安排送来瑞士,寄住在一户他们多年好友的家中。那家人待她客气,虽然没将她当成亲人,也没有故意疏远,日常起居由她自己打理。周言是这家人的儿子,比她年长几岁,当时已经在苏黎世大学读研究生。她一边读书一边适应语言和环境,也逐渐习惯了这个安静而清冷的家庭。
卢塞恩法学院毕业后,她选择留在瑞士工作。起初在一家事务所做合规辅助,后来短暂进入UBS投行部门实习一段时间。那时候,周言已经在瑞银总部的结构化金融部门任职,是一名产品设计师。两人朝夕相处,关系从最初的照应慢慢变成了一种默契。不张扬,不激烈,却带着一种生活流动下的安稳节奏。
结婚时没有铺张,只在苏黎世请了几位共同的熟人吃了顿饭,领了证,从此算是一起生活。
凌晨四点,电话响起。她醒来时还迷糊着,看到屏幕上是美国区号。电话一接通,那边传来周言压低的声音:
“我被捕了,在美国,需要律师。我在拘留中心,不能说太多。”
王瑶坐直身体,手机差点掉在地板上。她想问什幺,却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喇叭声和一声短促的指令。通话被挂断。
她没有慌张,只是慢慢穿衣服、洗脸、开电脑查航班,打给几位还未入睡的同事托人联系熟悉的刑事律师。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四小时。天还没亮,苏黎世湖上飘着一层雾。她戴上助听器,出门前从保险箱取出那本美国护照,塞进外套内袋。
飞机从苏黎世直飞纽约肯尼迪机场。她在商务舱靠窗位置坐下,把椅背放平,闭着眼听引擎的轰鸣。助听器开着最小档位,只为了让自己有种还听得见的控制感。
她18岁那年出了件事,从此再没踏上美国国土。那事之后,她被送往卢塞恩读书,音讯切断,没人问她愿不愿意。一夜之间,切换国家与语言,失去几乎全部联络人。现在,她在高空三万英尺的机舱里,靠着舷窗闭目养神,像是倒回原点。
抵达纽约时已是9月14日清晨。她从“US Citizens & Permanent Residents”通道入关,手中那本蓝色护照递给CBP官员,对方翻了一页,又擡头看了她一眼。屏幕上方滚动着电子字:“Welcome Home”。
王瑶收回护照,走出通道时没再看那行字。她离开这个国家太久了,这种“欢迎”显得突兀。
抵达曼哈顿下城区的联邦拘留中心后,她见到了辩护律师,是一位在白领犯罪案件中经验丰富的本地人,六十岁出头,言辞干净利落。他告诉王瑶,起诉方是南区地检署,主控检察官叫盛轩。
她愣了一秒,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那是十多年没被提起的名字。
当天上午,初次出庭。王瑶坐在旁听席,看见周言被法警押入法庭,穿拘留所发的蓝色囚衣,眼神疲惫但保持镇定。他朝她望了一眼,那一秒极短,仿佛只是确认她真的来了。
起诉方代表的身份很快被法官报出:Assistant U.S. Attorney, Xuan Sheng。
盛轩坐在起诉席,穿深灰色西装,脸部轮廓硬朗,头发剪得极短,眼神低垂看着手上的文件。他没有看王瑶,仿佛只是例行在审一桩金融案件。
在听证会上,盛轩主张拒绝保释。理由清晰:被告为外籍人士、无在美常住地址、金融资源充足,具备高逃逸风险。所有证据都符合法律语言,律师反驳空间不大。
休庭后,律师带王瑶去见检方,想私下争取一点协商可能。检察官办公室在Worth Street旧建筑五层,电梯缓慢老旧,走廊灯光泛黄。
进门后她先看到背影,盛轩站在窗边,手里拿着咖啡杯,正在看外头的街道。听见脚步声,他转身,视线落到她身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
律师做了简短介绍,留下两人单独说话。
王瑶没有开口。她站在原地,没有坐,也没有摘下助听器。
盛轩向她走近两步,说:“我们谈谈。不谈工作。”
“私人性质。”
“今晚八点,Balthazar。”
王瑶没答应,也没拒绝。
走出办公室时正值午后,外头阳光有些刺眼,街上车流噪声混杂。她戴着助听器,所有声音都异常清晰,像是刻意压过思维。
她叫了出租车。车窗上映出她的脸,模糊,带着些许疲态。
十年不见,他几乎没变,只是更沉静了。
她也不知道今晚是否应该赴约。
但她还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