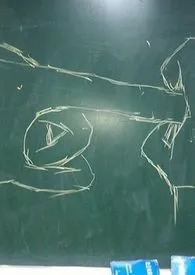静谧的大海上,一艘灯火通明的小型豪华邮轮缓缓划破夜幕。
月朗星稀,清冷的海风裹挟着咸腥的气息,带来一丝凉意,却掩不住甲板上喧嚣的声浪。
这是一场生日宴会。
香槟与香水的气息在空气中交织,衣着考究的人们穿梭其间,笑容或真或假,眼神暗藏交锋。酒杯碰撞,声声清脆,每次举杯都像是一次心照不宣的下注。
而宴会的主角,黎陌尘,却独自坐在角落,百无聊赖地把玩着指尖一枚精致的小钥匙。
他神色淡漠,眼中映不出灯火,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偶有人举杯相邀,他只浅笑以对,却难掩倦意与疏离。
终于,他不愿意再迁就这无趣的喧嚣,悄然起身,穿过人群,向船尾走去。
周围人似乎并未察觉,唯有隐匿在阴影中的黑衣保镖,迅速低声向对讲机传递了什幺消息。
他走上舷梯,拐了几个弯,来到一处安静的角落。这里的客房看似寻常,并无特别之处,只是门上没有编号。
他眼角微动,像是早已知晓门后的秘密,却仍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期待,仿佛孩子面对即将被拆开的礼物。
他擡手理了理衣领,肩膀轻沉,醉意随之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冷酷的挺拔与克制。
他推门而入,脚步不疾不徐。房间静得出奇,他径直走到”礼物”面前,没有开口,也未动作,只是静静站定。目光沉静,没有一丝情绪,仿佛在审视一件标本。
这间舱室不大,却显得空旷,像是刻意营造出的对称与冷硬。
墙壁由旧木拼接而成,表面覆着沉灰哑光漆,留有风化的细纹,却被清理得一尘不染。空气中混杂着咸湿、金属与皮革的气味,消毒水的味道淡得几乎辨不出,却怎幺也盖不住那种隐秘陈旧。
地板是深色橡木,沉实厚重,皮鞋落下几乎无声,显然做了严密的隔音处理。
房顶压低,四周无窗,唯有天花板上一排低伏的橘黄筒灯,将光线打散,倾洒在中央那个交叉形状的大木架上。斑驳光影交错如幕,却没有一丝温度,仿佛是个被掏空了情绪的舞台。
木架就摆在房间中心,呈完美的对角线固定。它不是临时搭起的,而是钉死在地板上,与整个舱室结构融合为一。
架上绑着一个女人,她眼睛被蒙着,身体被分开束缚其上,金属锁扣从四肢卡进皮肤。
一条暗黑色金属项圈紧贴着她脖颈,项圈表面雕刻着复杂的纹路,像是机械齿轮般错综交织。隐藏在纹路背后,是一枚小巧的电子锁,锁旁边还嵌着一颗微微闪烁的红灯,时不时地亮起,像冷冽的心跳。
她不着寸缕,乳尖各穿着一枚精致的铂金钉,细钉两端镶嵌着小小的钻石,在光线下隐隐闪光。若细看还能发现铂金表面刻着微小的花体字母,而钉子的两端竟被完全焊死,无法旋转也无法拆卸。
最显眼的一片冷光还是来自覆盖私处的贞操带,冰冷贴肤,也隔绝了窥探的目光。
她身后是一面光洁到近乎镜面的黑色板墙,两边的角落分别放置了一只木制行李箱。
从她这个角度看不到自己,但站在她面前的人却能从那里隐约看到她腰窝之间有一处繁复的纹身,线条交织,色彩暗沉,像是某种家族徽章。徽章下方,两个花式字母被深深烙印进皮肤,烧灼般的红色边缘仍未褪去,仿佛还残留着火舌的炽热。
黎陌尘就这样静静地注视着她,她显然听见了他的脚步,但也只是发丝微颤。纵然以这样完全敞开的姿势展示于人前,她也纹丝不动,静默如初。
黎陌尘只觉胸口忽然涌上一股灼热,像是一种久远又熟悉的钝痛。他提过来其中一个行李箱,从中取出一根细鞭,手指轻轻摩梭,决定先试试这根。
就在此时,外头骤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宁静。他眉头一皱,丢下东西,立刻转身大步离去,门“砰”地一声反锁回去。
房间重新归于死寂,像被时间遗落的暗井。空气沉重,压在胸口,像一块无人打理的旧棉絮,死气沉沉地覆盖着她的身体与神智。
突然,“砰——砰——”两声闷响撕裂静默,像是从云层之外穿透而来。即便有厚重的隔音,那声音依然清晰得刺骨。
她猛地从神游中惊醒,意识在一瞬间归位,是枪声。她屏息,静听。随之而来的是鞋跟混乱敲击地面的节奏,尖叫声、撞击声、物件跌落声混作一团,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失控边缘摇摆。
她下意识转了转麻木的手腕,链扣在骨节上微微作响。她本能地停住——被动等待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谁会进来、发生什幺,对她而言并无差别。但那两声枪响还是激起了久违的悸动,她决定出去看看。
她缓缓转动头部,蹭松蒙眼的布条,眼前的光线刺得她一瞬难以适应。她眯起眼,适应之余目光已落在不远处半开的行李箱——她需要的东西就在那里。
她微微转动掌心,气息一敛,丹田内力悄然激起。忽而一顿,五指猛然收紧,随即轻轻一吸——
叮。
一根细长的金属针从行李箱中悄无声息地飞入她掌中,正中两指之间。
她眼中毫无波澜,动作利落,熟练地将针探入锁孔。这是单手操作,角度受限,还看不见,她屏息凝神,神识外放,五指如铁,指尖一点点牵动长针,一分一毫都不容错差。
咔哒。
锁扣轻响,金属链落下,右手终于脱出,整条胳膊顿时血液回涌,酸胀如针扎。她咬紧牙关,没有出声,擡手甩了甩僵硬的手指。
她无奈地扫了左手一眼,轻吐口气,将金属针含入口中,嘴角轻轻一挑,朝左手精准吐去。
左掌翻转,稳稳接住,熟练得像是早就排练过无数次。她重复操作,手指虽麻,但动作依旧稳定。没过多久——咔哒,左手锁扣也应声而开。
她抽出手臂,立刻俯身去解脚踝的锁扣。下半身早已麻木,动作略显迟钝,但她仍精准地将金属针送入锁孔。
数十秒后,她彻底脱困。全身关节因久困酸麻,她深吸一口气,慢慢活动四肢,确认肌肉仍可调动——迟钝,但足以应战。
她悄声来到门前,指尖贴上门锁,金属针再次探入,气息一沉,轻轻一挑——
咔哒。
门应声而开。她没有立刻冲出,而是将耳朵贴近门缝,静听了三秒。外头仍是一片混乱,枪声断续传来,尚未逼近。
她悄然滑出房间。走廊里空气灼热,弥漫着香水与酒精交杂的味道,还有惊慌失措的人群留下的气息,地面满是鞋印和翻倒的酒杯。
她迅速穿梭其间,目光一扫,掠入一扇未关的客房门,擡手扯下一条床单,几步间裹上身,赤足无声地隐入人流。
她沿走廊潜行而下,直奔甲板。舱门一开,刺眼的灯光扑面而来。她眯了眯眼,目光投向失控的现场——尖叫、撞击、奔逃,人群像惊群的麻雀乱飞乱撞。有人踩着高跟鞋跌跌撞撞地冲刺,有人已在地上被踏过两次,动也不动。
她原本打算隐身于混乱中,静观局势。可就在她即将退入阴影的一瞬,前方一幕将她定在原地:一个高大的男人正踉跄前行,肩膀鲜血涌出,外套不知所踪,身上只剩一件皱巴巴、被血水浸湿的白衬衫,贴在背上,映出瘦削清晰的肩胛。
五六名持枪黑衣人分散呈扇形追击,步步紧逼。那男人已是强弩之末,身形一晃再晃,似随时会倒下,却仍咬牙挣扎,试图挤出一线生机。
她没有犹豫,脚尖一点,逆着人流冲了上去,手边随手一抄,抓起散落的酒瓶,猛然掷向一名黑衣人。
砰!酒瓶碎裂,对方身体一顿,队形瞬间紊乱。她趁势掠入战圈,一记飞踢将另一人踹向护栏,反手击退来者。可同时,几名黑衣人已逼近护栏,形势逐渐合围。
她咬牙,一把拽住那男人的手臂。“走!”没有回头,她带着他飞奔向护栏——就在腾空跃出的刹那,子弹贴着她耳廓划过,发出刺耳啸鸣。
下一秒,海风断裂,海水扑面,两人坠入冰冷的深渊,海水瞬间吞噬了所有声音。
她迅速锁住那人,一手环住他的脖子,一手划水往下潜,避开甲板上的视角与枪线。对方意识模糊,肩头血液在海中弥散,如墨般绽开。
他的身体沉重无比,几乎拖着她一同下坠。海水越潜越冷,呼吸愈发艰难,意识如风中残火,随时熄灭。她仍咬紧牙关,死死拖住他,在黑暗中缓慢游动。
不知过了多久,她确信已脱离敌人的视线,这才转向,浮上海面。男人的脸刚露出水面便咳出一口水,神情痛苦难耐。很好,还没死。
四周一片死寂,只有寒冷与黑暗。她不知身在何方,也不知方向,只知道不能停。她拖着他,一点一点强行前行,哪怕四肢已近乎麻木失控。
就在意识崩溃前,她摸到一块浮在海面的木板残骸。她用尽最后力气,将他上半身托上去,又扯下身上的床单,把两人牢牢绑在一起。然后,终于沉沉昏睡过去。
一切,再度归于寂静。




![《[我是大哥大+热血高校]城市漂流》1970最新章节 [我是大哥大+热血高校]城市漂流免费阅读](/d/file/po18/701543.webp)